有人認(rèn)為,這是一幅畢加索晚期的帶有自喻色彩的作品。
盡管畢加索曾嘲笑過那些試圖去理解他的藝術(shù)的人:“人人都想理解藝術(shù),為什么不設(shè)法去理解鳥兒的歌聲呢·”(他認(rèn)為繪畫是無法用語言“解釋”清楚的)——但“語言,作為存在的家園”(薩特),仍然是迄今為止人類解讀藝術(shù)的最好的“鑰匙”。 在《花瓶邊的男人和女人,半身像》中,男人的形象是畫家描繪的主要對(duì)象——盡管看起來女人頭在男人頭的前面,而且雙方軀體的錯(cuò)位使二者顯得更加難分難解,渾然一體,但男人形象的主體性在整個(gè)畫幅中依然相當(dāng)明顯。他那卷曲而狂亂的發(fā)型、輪狀的皺領(lǐng)和披肩,使人想起在60年代晚期以來畫家最常用的“步兵”的表現(xiàn)手法——它被認(rèn)為是畫家的自畫像的隱喻手段之一。但更為豐富的是這位“步兵”的表情:他癟著嘴巴,鼻子扭曲,兩只眼睛朝背向女人的那一邊望過去,一臉的悶悶不樂——顯然,肉體的緊密結(jié)合無法掩飾他們內(nèi)心的矛盾與沖突。女人在畫中處于一個(gè)相對(duì)弱勢(shì)的位置,她無助而充滿著誘惑。 畫中右邊五斗柜上的花瓶和綠色的植物看起來非常抽象,充滿生機(jī)——它與其說是一種裝飾,不如說是畫家在“老之將至”時(shí)的自我激勵(lì)。
作為20世紀(jì)最偉大的藝術(shù)家,畢加索一生都在不停地變換著創(chuàng)作風(fēng)格,用他自己的話說,是對(duì)風(fēng)格的不斷地“發(fā)現(xiàn)”。在創(chuàng)作《花瓶邊的男人和女人,半身像》時(shí),畫家已89歲。但從畫家對(duì)作品中人物的臉部等部位的處理手法來看,我們依然可以找到他早期的立體主義風(fēng)格的影子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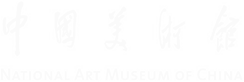

 油畫
油畫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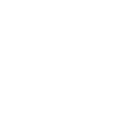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 京公網(wǎng)安備 11010102007210號(hào)
京公網(wǎng)安備 11010102007210號(hào)